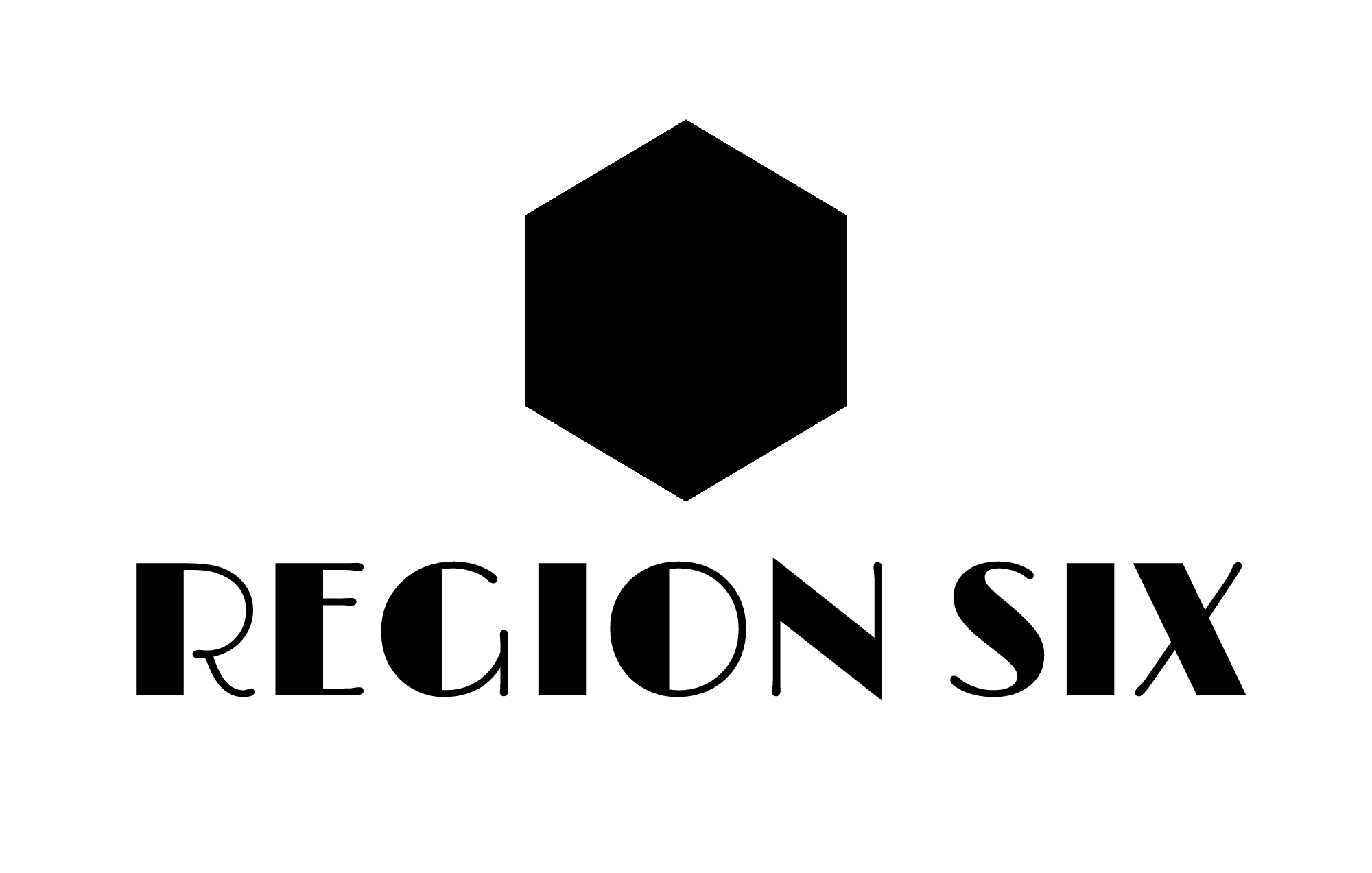"I will not act before understanding. Context is everything." 这是 Alfredo Jaar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再三强调的一句话。周二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看到了他在日本、加拿大、美国、芬兰等地的艺术项目,就像上了一堂关于现代艺术的大师课。主题都与政治、民生有关,用大量的幻灯片结合一部分视频介绍,好像在两个小时里亲身来到了这些地点。"It Is Difficult"的名字与他的一本书同名,书封面上的越南小女孩出现在幻灯片每个章节中。这个项目在最后被提到。
1. We Shall Bring Forth New Life
Jaar 受邀为日本创作艺术项目以纪念东日本大震灾。他去了四次,在一片废墟的福岛看到当地的灾民依然努力地试图复原自己原先的生活:居民在集装箱做的临时住所里种些小花小草、当地的报社用手写的方式坚持播报新闻。最让他感到触动的是两栋建筑,一是残留下的广播站,正是在那里一名女记者呼喊指挥当地居民逃生,并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个是重灾后遗留下的小学,校园内的几十块黑板都保存完好。他粗略地计算了学生的数量,得出这样一个数字:在福岛遇难的学生们一生面对这些黑板所度过的时间总计 15,000 个小时。
生ましめんかな(We Shall Bring Forth New Life,且容我给你新生)取自日本反核反战女诗人栗原贞子的同名诗。1945 年,栗原贞子亲身经历了原子弹爆炸。这首诗是原爆期间她目睹邻居在废墟中分娩后创作的。产婆在接生后体力不支死去,而新生儿活了下来——“且容我给你新生,纵然舍弃我之性命”。Jaar 请不同的小学生书写“生ましめんかな”,投影在从校舍取来的那些黑板上。黑板前堆放的粉笔也是从学校收集来了,在黑暗中营造出“生命,色彩”的感觉。
最近,面对民众放弃核电的反对声,日本政府还是决定重启核电来减少电力成本。
2. Skoghall Konsthall



瑞典的这个项目比较好玩。Jaar 也是受邀来到名为 Skoghail 的 8 万人瑞典小镇创作艺术项目。小镇的一切都全部由造纸厂建造,提供资金:教堂、住宅、学校等等,甚至连乐队也是造纸厂的工人。但三十年来他们没有任何展示当代艺术的空间。Jaar 于是倡议政府提供资金,用造纸厂提供的木材和纸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纸质博物馆。里面展出的是 Skoghail 年轻艺术家们的作品,还让小孩们在空间里创作折纸雕塑(在纸镇的纸博物馆里做纸雕)。其中有位艺术家做了 50 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你怎么能忍受在三十年里小镇上都没有博物馆呢?结果有许多人回答说:我觉得这没什么啊。
围观博物馆的人很多,开幕时什么都看不见。Jaar 原本计划在 24 小时之后把博物馆烧掉。可因为博物馆很受欢迎,当地政府要挟“你要烧的话,我们就呆在里面不出来。”最后,Jaar 同意给小镇免费设计一个游乐场,政府才肯答应。“我想给这个不需要当代艺术的小镇看一下什么是当代艺术,他们看过之后,我就把它拿走。”于是,他就让消防队在众目睽睽下把这个博物馆烧了。
七年后,Jaar 又接到 Skoghail 政府的电话,请他作为建筑师为该小镇设计一座永久的博物馆,预计在 2018 年开放。
3. One Million Finnish Passports
《一百万份芬兰护照》是 Jaar 于 1995 年在赫尔辛基创作的作品,是对当时芬兰新移民政策的回应。芬兰是反移民呼声很高的国家,在作品诞生前的十年,瑞典、丹麦和挪威的移民人数超过了一百多万,而芬兰只有 17 个。Jaar 在律师的帮助下,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印刷了一百万份芬兰护照。这些护照被移民局要求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观看,好像玻璃监狱一样。
Jaar 说,观众中有一个人的反应特别令他感动:一个芬兰小伙在看完这个作品后跑回家,拿了他自己的护照后再来到作品前,趁保安不注意把自己的护照丢了进去。
这一百万份护照被政府要求在展览结束后烧毁,烧毁过程中不能留下任何影像记录。不过,Jaar 后来偷偷拿掉了 200 本,说自己不知道要拿它们做什么。
4. Lumières dans la Ville
在蒙特利尔标志性建筑 Marché Bonsecours 中他也做了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作品。Marché Bonsecours 在历史中被共被烧过 5 次,每次烧毁后都被重建,于是没人敢在在里面办公了。Jaar 受邀利用这个空间创作,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了穹顶附近给流浪者免费提供食物的箱式货车。在这家机构,流浪者不用提供任何证明就可以获得食物。从流浪者那里得知,他们在蒙特利尔是“无形”的人群,政府和路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而且这样的情况在全加拿大都很平常。
Jaar 觉得,人们忽视流浪者的问题就像摧毁穹顶的大火一样在蚕食这座城市。于是,他就在穹顶里装了近十万瓦的红灯。每当有流浪者去机构下三家庇护所按门铃的时候,穹顶里的灯就会闪烁一下,好像被火焰点亮一样,让在繁华街区消费的路人难以忽视。接着,有年轻的流浪者整夜围绕在庇护机构门口长时间地按按钮,让红灯整晚通明。当十几家慈善机构想要参与进来的时候,蒙特利尔的政府叫停了这个项目,把灯熄灭了。
5. Everything I know I learned the day my son was born
又是一个与移民问题相关的作品。Jaar 受邀为达拉斯的 Nasher Sculpture Center 创作来庆祝雕塑中心十周年。在走访了当地大街小巷后,Jaar 发现雕塑馆正处在达拉斯中心,所在的是一片富裕的白人区,平日里来参观这家雕塑馆的也基本是白人中高产阶级。居住在靠近达拉斯边缘的有色人种大多数一辈子都没有进过馆内。
他想,与其来庆祝雕塑馆的生日,不如来庆祝那些从未来到过这里的人们的生日。Jaar 与当地三家接待有色人种为主的医院达成合作,在产房录下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上百个家庭都参与了进来。这些啼哭声会在展览期间一直在这座绿色建筑中回放,此起彼伏,像一件音乐作品。每位参与进来的家庭成员都能获得该博物馆的一年会员,而收录啼哭的宝宝则能成为终身会员。“他们第一次进入这个博物馆不是以观众的身份,而是以艺术家的身份,” Jaar 说。
6. A Hundred Times Nguyen
讲座接近尾声,Jaar 终于提到了图片中小女孩的故事。在九十年代,大批越南移民通过船只来到香港寻求战后更好的生活,有一大部分难民被香港警方扣留,居住在混乱不堪的难民营里。这十五万移民面对的是当撒切尔下达的遣送回国的威胁。Jaar 当时在那里呆了十天,造访难民和难民署。期间有个小女孩一直跟着他,但不说话。他经过女孩的同意给她照了五张相,每张间隔 5 秒钟。记下了她的名字:Nguyen Thi Thuy。他猜想女孩应该和其他每个月出生的三十多个孩子一样,是从小在难民营长大的。之后,他伸出了手,女孩握住了,并再也没有松开,一直到 Jaar 离开难民营。
Jaar 说,在香港拍的成千上百张照片中,小女孩的脸是最让他难忘的。他发现,这一连串的照片中,女孩的嘴角从腼腆到笑容逐步过渡,头抬起来了,最后正视镜头,虽然还是微笑着,但似乎也带着忧伤。他将按照不同的顺序排列,印刷了 100 张——起名为 A Hundred Times Nguyen。
最后,他引用了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标题:《教我们从疯狂中蜕变》作为结语。同时也是他的行为艺术作品——走到纽约街头,在身体前后绑上写着“Teach Us To Outgrow Our Madness”的黑板,并询问路人如何从疯狂中蜕变。
“The only space of freedom left, is the space of culture. And culture, can affect change.”
讲座结束后我问他小女孩长大后有没有找过她,他说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能再联系上。
非完整录音在这里(百度盘)。前面一部分有本人骚动的声音,不过后面大体是清晰的。翻译一开始不想录,但后面因为停顿太频繁,所以还是录进去了。口译的水准还行,除了有把“广播台”翻成“核电站”,把“瑞士”翻成“瑞典”的低级错误,总体没有硬伤。但翻得累赘,还是建议看看文字就行了。反正要求现代人听一个小时的音频是很困难的。